女教师一学期被学生家长举报十几次:听到理由都想笑
记者/梁婷 实习记者/卢倩莹 林珂莹
编辑/计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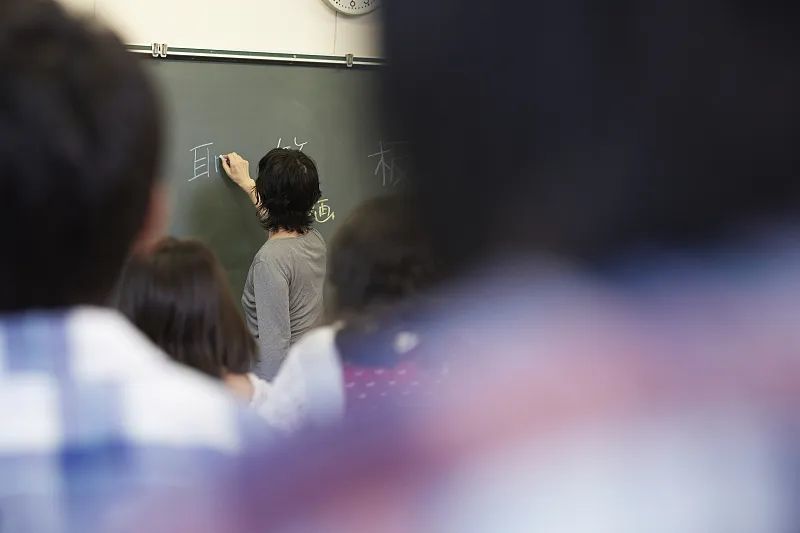
广州一所小学的新生家长会上的PPT
自证、自查
一旦被举报,老师们要反复自证清白。临近暑假,快放学的时候,男朋友给李萌点了一个包装精美的水果外卖,她到校门口取的时候,被接孩子的家长看到了,他们看着她说笑,“没结婚的小姑娘就是舍得给自己花钱”。不出意外的,她又被举报了。理由是,收了学生家长的礼物,可能对学生搞区别对待。
光有订单截图证明不了这是男朋友买的,她不得不把男朋友找来,出镜录制视频,同时点开外卖软件,找到订单,证明这是男朋友本人的手机页面。然后再把视频一级一级向上汇报。
又一次,在李萌以自己要去医院看病为由拒绝那位妈妈提出的送孩子要求后,新的举报又落到她身上:“老师有传染病还坚持上课”。主任让她去医院体检,并上交一份体检报告。
还有一些摆在台面上的举报,对于老师来说,更难自证清白。
小学音乐老师王欣悦参加工作不久,在组织一次考试时,和家长有了冲突。那是一场游戏形式的考试,协助维持秩序的家长本不应该进入考场,但有几个家长跟着孩子进来了。考试时间到,她催促家长和孩子离开时,一位家长表现得很生气,“你怎么那么凶、那么严厉”。王欣悦承认,自己当时嗓门确实比较大,现场太混乱,其他等待考试的小孩又不断涌进来。她没想到,几位家长在考试结束后,先是在群里攻击她“没师德,不能惯着她”,又以她打骂小孩为由给教育局打了举报电话。
而这一切的证据,是家长和小孩的一段录音。妈妈问孩子,“你们音乐老师怎么对你的,是不是欺负你了?”小孩回答,“老师打我、虐待我”。
“你是在故意引导,小孩知道你想问什么。”——校领导帮王欣悦解了围,这也是整件事唯一让她觉得感激的地方。
王欣悦向家长解释,录音里说自己被虐待的小孩,在课上一直和同桌说话,自己让他站起来,小孩不理会,还说“关你什么事,我就不站”。她当时有点生气,拿起桌上的本子拍了孩子的头。但家长并不接受。
“虐待真的是谈不上。”王欣悦很委屈。后来,她听年级主任说,这几位家长还在四处打听,想要搜集她苛待小孩的证据。如今,这件事就悬在那里。王欣悦说,最难熬的是,你会不停地想家长说的话。原来教师这个职业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受人尊重。好在,她感受到了学校对自己的保护。
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并没有这种“运气”。有一次,她被学生举报,监考时给自己班学生传答案。“我都没法解释,哪个脑壳正常的老师会在月考传答案?而且我也得知道答案才行,我自己都不会”。她说,年级主任虽然相信这是个误会,但依然坚持,既然有学生提出来,就是她做了让学生误会的事,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
她对学校和学生都很失望,“学生,我还可以解释他们年纪小不懂事,但学校领导居然连这么扯淡的事情都让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”。她写了辞职报告,但被组长拦下了,实在很缺语文老师。
这位老师所在的学校专门设置了一个名为“表白墙”的QQ群,初衷是“想要给学生发泄的空间”。有一个领导每天负责浏览“表白墙”,一旦发现有老师被提及,立刻找来谈话。在这个群里,常常有人“投诉”老师。“表白墙”的出现,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矛盾。
在应对举报问题上,学校看起来力不从心。在李萌之前,班里的英语老师因为受不了被无故投诉,哭着找到校领导,最后只能是换了年级。李萌接连被举报之后,年级主任给她的饭卡充了200元,以示补偿,还给她放了几天假,也问过要不要换年级,李萌觉得无所谓,她说,“再熬两年,大家都会走的,就过去了”。
9月初,在广州一所小学的新生家长会上,一位校领导的PPT更直白地诠释了这种无力。其中一页写着:“提醒几件事,不要随意投诉,因为投诉的都考不上高中”。图片很快被发到了网上,当晚,属地教育局发布通报称,经过核实,学校的确有不当用语,已严肃批评了当事校领导。通报的另一句解释为这件事增加了某种荒诞感——学校的本意是希望家长对于学校能够多些理解、支持与包容,培育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。
“跪着的老师,真的教不出站着的学生”
通过举报来遏制老师违规收礼、虐待学生、性侵等行为,接受采访的老师们都很支持。但在更日常的校园生活中,她们遇到的,大多是琐碎的、甚至有些离谱的理由。
“没啥工作热情了”,李慧丽每次做事情都会下意识斟酌,她“不是很敢教育”学生,尤其之前举报过的,更不敢多管,也会减少找家长的次数。李萌也坦诚地说,理智上知道孩子没做错什么,但她常常会冒出“突然不想看到他”的想法。
李萌最无法接受的是,“举报者即便是诬告也没有代价”。学生、家长随口说一说自己的猜测,或者只想发泄情绪,并没有意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后果。
边亮所在的学校,面对举报,已经很积极应对,但依然面临很多无可奈何。
一位入职不久、“98年”的班主任被学生匿名举报“言语粗暴、恶毒,经常打学生”。接到举报第一时间,边亮找到这位老师。他已经很注意谈话的用词,都没提举报两字,只是说,最近有学生反应,在语言上,可能有暴力倾向,如果有的话要改……女孩先是错愣,然后就开始哭。
他和分管德育的主任找到这个班的学生,组织座谈会。这位老师确实要求严格,但并不存在举报中提到的内容。他们的调查结果被主管部门打了回来——接到举报的是省长信箱,得找到学生继续详细沟通。对学生的信息一无所知,为了解决问题,主管单位把姓名告诉了边亮。
边亮小心地打消顾虑之后,学生才说,他和这位老师其实并没有交集,只是听到有人议论,义愤填膺,觉得“看不惯”。
不可否认,举报和投诉是每个人的权利,也有利于改进教育教学行为,但除去一部分真的存在师德师风问题的老师,很多被举报的,可能是那些负责任的老师。边亮说,他们学校曾经有一位教学成绩很好、很受家长认可的老师,一直当班主任。经历了两三次被举报之后,虽然都和家长沟通好了,他都坚持不带班,“就做个科任老师,上完课,改完作业就行了”。
“一旦出问题担不起这个责任”。付建国告诉深一度,现在大小会议上都在和老师强调,首先要保证“安全第一”。更通俗的理解就是,“你教不好学生,他考不上大学,你没有错,但是他安全出问题了,你就有错了”。他说,“如果老师更自私一点,只负责上课下课,学生有什么其他事都跟我无关,你爱听就听,不听就不听。这种老师不好找毛病,他也不会被举报,很安全,但这种老师并不是真正有情怀的老师。”
如果证明是不实的、扩大化的举报,为什么不能去批评学生、告诫家长,是非判断不也是教育的责任吗?
——对于我的提问,从业23年的边亮很无奈,“现在的教育就是忍辱负重,甚至有点卑微”。即便是不实的举报,他们“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抚家长情绪,不要再举报了”。“批评是不可能的,甚至一点言语上的刺激都不行。只能去安慰老师,做老师的心理疏导:既然有质疑,以后就优化”。很多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,但一个巨大的忧虑一直萦绕在边亮内心,他反复说了几遍:“跪着的老师,真的教不出站着的学生”。
今年的8月31日,边亮的信心终于有了一些提振。教育部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,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,要对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,公开正名;对恶意歪曲事实,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回击,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。这是边亮从教23年中,第一次听到的关于不实举报要正面回应的“硬气”表达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)
编辑:一起学习网
标签:老师,家长,学生,学校,孩子,的是,楷体,自己的,这是,教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