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绍东:驳“长城以北非中国”论
作者:王绍东
来源:《历史评论》2024年第3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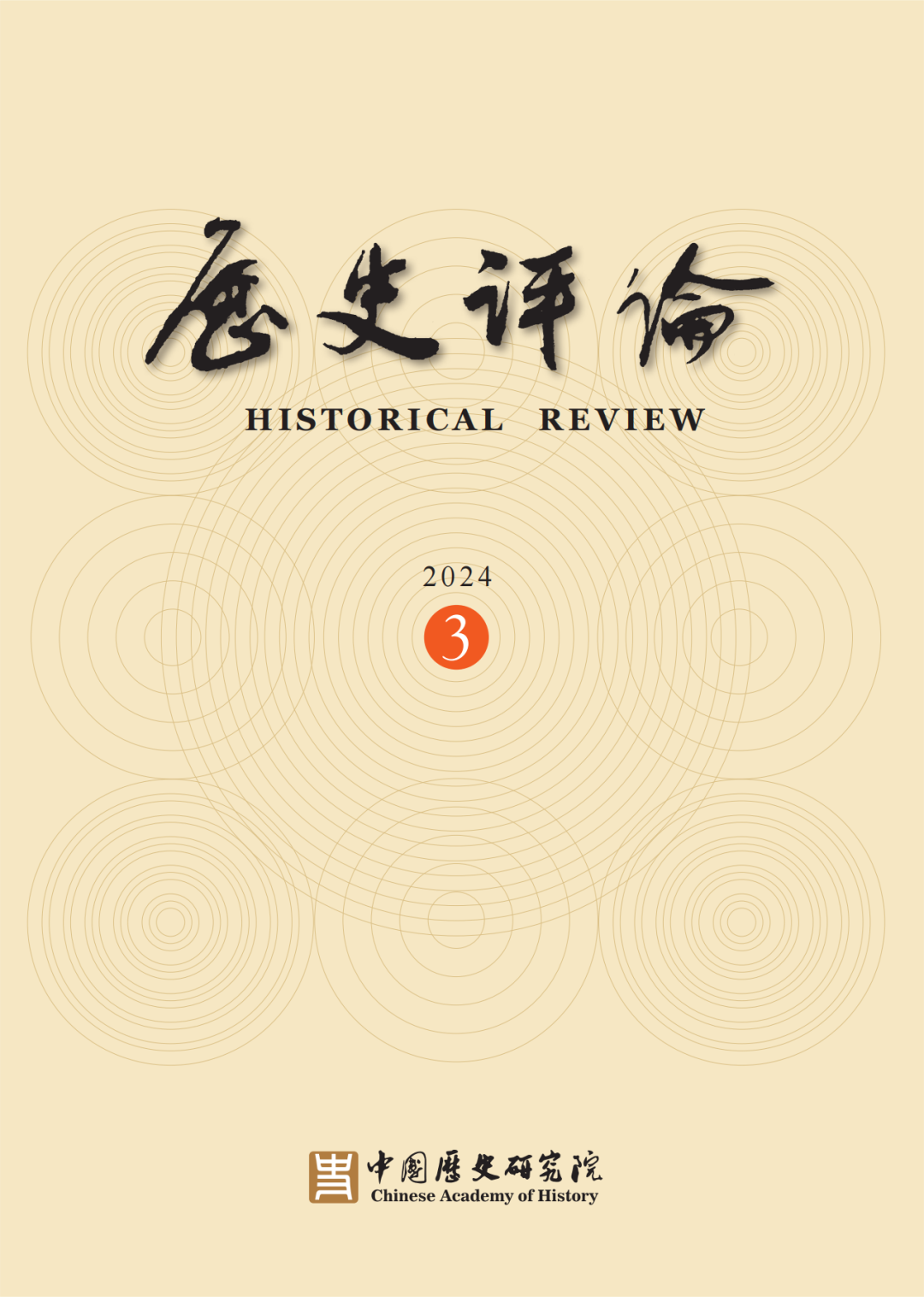
辽道宗哀册为汉字、契丹字各一合,展现出辽朝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吸纳。图为辽宁省博物馆藏辽道宗汉文哀册册盖,书“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” 刘朔/供图
元朝作为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“大一统”政权,同样认同自己是“中国”正统谱系中的一员,将“中国”视为华夷混一、各民族共有的“中国”。在编修史书时,元朝将宋、辽、金均视为正统,使“中国”的内涵更加丰富。清朝也是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“大一统”王朝,其统治者强调“华夷一家”,认为做“中国”之主者不在于是华是夷,重要的是以德配天。雍正帝宣称:“盖生民之道,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。此天下一家,万物一体,自古迄今,万世不易之常经。”清朝认同的“中国”,超越地域与民族界限,是当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状况的反映。
长城内外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疆域
在古代历史上,“中国”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,不能套用近代民族国家理论来解释。夏商周时期,君主直接控制的王畿之地被称为“中国”,与诸侯国及周边夷狄五方之民生存之地共同构成具有疆域含义的“天下”。春秋战国时期,长城以北的匈奴、东胡等游牧民族,以“逐水草迁徙”的方式经营着北方草原。匈奴统一草原地区,并与秦汉政权对抗。汉匈间先以“兄弟”相称,之后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,其控制的广阔地区也成为汉朝疆域。戎、狄、羌、月氏、匈奴、东胡、乌孙等草原民族与汉族共同开拓了中国的北方疆域。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,北方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建立政权。这些政权以“中国”自居,自认华夏,以实现统一为历史使命。前凉、后凉、南凉、北凉控制了河西地区,后燕、北燕控制了辽西地区。一些政权的统治区域则跨越长城内外,如氐族建立的前秦、鲜卑建立的北魏一度统一北方。进入中原的各游牧民族逐渐转变生产方式,接受中原政治制度,学习儒家文化,实现深度的民族交融,为隋唐“大一统”创造了条件。唐朝在边疆地区采取郡县制与羁縻府州制并行的治理方式,将长城南北的广大区域纳入管辖范围。这一时期,中原王朝及各北方民族政权所控制的地区,自然属于中国的疆域。
契丹、党项、女真建立的辽、西夏、金政权的统治区域兼具游牧区与农耕区,他们都认为自己控制的区域是“天下”的一部分。有学者指出,他们与宋朝之间的疆域,“只是军事防御的界限,依然并不具有近现代国界的性质”。蒙古人建立的元朝,将疆域扩展到超越汉唐的空前范围。“若元,则起朔漠,并西域,平西夏,灭女真,臣高丽,定南诏,遂下江南,而天下为一。故其地北逾阴山,西极流沙,东尽辽左,南越海表。”
明朝自认是“中国”,同时亦有蒙古、女真政权自称“中国”的记载,无论是明朝还是蒙古、女真政权所管辖的区域,无疑都属于历史中国的疆域。清朝以“大一统”观念经营边疆,除全面扩展郡县制的实施范围外,还在东北实行“三将军”制,在内外蒙古实行盟旗制,在西北设置“总管伊犁等处将军衙门”,在西南地区“改土归流”,在台湾设立“台湾府”,推动空前的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,使中国的疆域由此前的“有疆无界”变为了“有疆有界”。
中国北方疆域是在长城内外各民族长期联系、互动中形成的。谭其骧指出:“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汉族是汉族,中国是中国,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,这是不同的概念。在1840年以前,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,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。”无论是北方民族建立的“大一统”政权还是地方政权,都为中国疆域的开发、建设、守护、拓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。
持“长城以北非中国”论者,或由于对中国传统的国家观、疆域观以及多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认识不清,以致将历史上某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域当作中国的疆域,或无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特点,将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套用于中国历史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日本学者抛出“满蒙非中国”论、“北亚历史世界”论,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张目。近年来,不断有欧美学者将“长城以北非中国”的理论包装上学术外衣,以不同的形式加以宣扬,将汉族与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对立起来。无论出于何种动机,“长城以北非中国”论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观点。
作者单位: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
编辑:一起学习网
标签:长城,中国,中原,政权,疆域,游牧民族,内蒙古自治区,北魏,王朝,汉族
